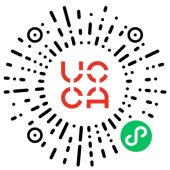UCCA北京
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
2025.9.27 - 2026.1.4
关于展览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2025年9月27日至2026年1月4日呈现“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本次展览将呈现艺术家近二十余年的艺术实践与探索,并聚焦2020年之后创作的作品。在“临时共同体”中,观众将进入一个因短暂相遇而持续发生变化的现场,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联系,并由此想象共处和团结的另一种可能。
2025年9月26日至2026年1月4日,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呈现日本当代艺术家田中功起个展“临时共同体”。本次展览呈现田中功起(1975年出生于日本栃木市)近二十余年的艺术实践,展出包括其早期影像在内的十余件作品,同时还将首次呈现一件由UCCA委任创作的全新作品。展览聚焦艺术家如何在临时性的聚集与开放性的协作中探寻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由偶然、危机或实验触发的相遇往往短暂,却在不确定与矛盾中显露出情感的流动与张力。展览并不提供明确的答案,而是通过营造情境,让观众在与他人“临时”的共处中体会这一关系的可能。“田中功起:临时共同体”由UCCA策展人张南昭策划。
田中功起的创作从最初关注物与物的关系,逐渐转向人与物的互动,最终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他擅长使用影像、摄影、场域特定装置以及特定主题的工作坊,捕捉那些日常、易被遗忘和忽略的行为、物品与观念,通过偶然的组合或去功能化的处理,揭示潜藏其中的意义与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普通物件与动作不仅是被观察的对象,也是引发观众重新感知与思考的媒介。
在早期创作阶段,田中功起聚焦日常物品的物质性,以此打破既定的认知框架。在《123456》(2003)中,一个骰子在玻璃瓶中不断滚动与碰撞,影像与声响交织成近乎无尽的循环。作品以重复与偶然构建非线性的观看体验,将微不足道的细小动作转化为关于对流动与不确定性的感知。《看着水消失》(2006)以几乎静止的画面捕捉水分蒸发过程,将观众置于一种冥想式的观看状态:这件极简而近乎无事发生的影像令流逝的瞬间成为唯一的风景,时间成为最核心的媒介,存在的脆弱性与转瞬即逝被无限放大。《一切一切》(2006)则记录了艺术家与助手在街头对日常物品的即兴演绎——扫帚、卷纸、床垫等从原有的用途中解放,成为既游戏化又暗含抵抗性的媒介,引发观众对于物与物、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些作品以试验性的姿态,预示了田中功起之后对于集体经验与社会关系的持续探索。
自2011年起,田中功起逐渐将创作重心转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组织多人参与的“工作坊”探索在临时聚集的群体中,个体经验如何在其中流动、碰撞与消融。他并不以传统意义上的“创作者”自居,而是充当一种“时刻”的促成者——设定情境、退居观察,让参与者在无法完全控制且难以预测的过程里,共同构建一个临时的微观社会。本次展览呈现的三件代表作品揭示了这一创作逻辑的多重面向:《五位钢琴家同时弹奏一架钢琴(初次尝试)》(重剪辑版)(2012/2025)将原本的独奏行为转化为必须协商、适应与调解的合作现场;《五位诗人同时写一首诗(初次尝试)》(重剪辑版)(2013/2025)在共同创作的语言张力中捕捉个人风格与集体成果的矛盾交织;《五位陶艺师同时制作一件陶器(静默尝试)》(重剪辑版)(2013/2025)呈现了个体意识在群体创作的共同焦点中逐渐消融的状态。多人参与下的复杂关系与心理状态层层显现,一种消逝与重生的可能由此出现:当所有人专注于同一个目标,个体的存在似乎在某个时刻消失了,留下的只有纯粹的群体行动。
近年来,田中功起的影像实践持续向更普遍的育儿、上班族等社会议题延伸。《省思笔记(重组)》(2021)改编自艺术家的随笔集,通过重组影像档案与文字,思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并提醒着观众真正的改变始终来自个体与社区间的细微联结。个体经验与公共辩论在《迁徙与毁灭》(2024)中交织,作品以多学科对话为基础,引导观众思考如何在持续变化的世界寻找跨越国界与物种的共生可能。《表演即分享自我》(2025)围绕性别角色、家庭分工与职场权力关系展开,揭示个体面对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差异的现实困境。由UCCA委任创作的最新作品《10年》(2025)召集此前参与过艺术家作品的多位叙述者,通过他们对个人记忆与社会事件的讲述,呈现过去十余年间私人生活与公共历史的碰撞。
本次展览在空间设计上也延续了“临时共同体”的主题。作品的屏幕不依附于固定墙体,而是被安置在简易木质结构上;展厅中散落的椅子可被观众自由移动。观众因而可以在观看过程中随意调整观看视角,或即兴地自发聚集,或独自停留。空间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使展览本身也成为一个不断生成、又随时可能瓦解的“临时共同体”。
关于艺术家
田中功起1975年出生于日本栃木市,现工作和生活于京都。2000年,田中功起获东京造型大学艺术学士学位;2005年,获东京艺术大学艺术硕士学位。主要个展包括“脆弱的历史(一部公路电影)”(善宰艺术中心/首尔、米格罗斯博物馆/苏黎世,2020/2018);“不确定任务”(镜花园,广州,2019);“临时性研究(工作标题)”(格拉茨美术馆,格拉茨,2017);“陶艺家与诗人”(亚洲艺术博物馆,旧金山,2016);“田中功起:在一起的可能性,以及实践”(水户艺术馆,日本茨城县水户市,2016);“脆弱的叙述者”(德意志银行美术馆,柏林,2015);“抽象的叙说——共通的不确定性与集体行动”(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日本馆,威尼斯,2013)等。他的作品也在群展和双年展中广泛展出,包括“抗体”(东京宫,巴黎,2021);“纵使黑暗,我仍歌唱”(圣保罗双年展,圣保罗,2021);“正确方向的每一步”(新加坡双年展,新加坡,2019);“情的时代”(爱知三年展,爱知县,2019);“行动!”(苏黎世美术馆,苏黎世,2017);“艺术万岁”(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威尼斯,2017);“生存痕迹”(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北京,2016);“M+进行:流动的影像”(M+,香港,2015)等。田中功起的作品被诸多美术馆收藏,包括香港M+、日本东京森美术馆、荷兰凡艾伯当代美术馆等。
赞助与支持
展览独家环保墙面方案支持由多乐士提供,独家音响设备与技术支持由真力提供。同时亦感谢尤伦斯艺术基金会理事会、UCCA国际委员会、UCCA青年赞助人、首席战略合作伙伴阿那亚、首席艺读伙伴DIOR迪奥、首席影像伙伴vivo、联合战略合作伙伴彭博,以及特约战略合作伙伴友邦保险、巴可、多乐士、真力、北京SKP和Stey长期以来的宝贵支持。
展览公共项目
展览开幕日,艺术家田中功起将首先带来一场关于其艺术实践的分享,随后与此次展览策展人张南昭及作家、编辑、译者安德鲁·梅尔克尔展开对话。三人将围绕展览内容,聚焦跨语言与跨文化实践在艺术创作中的转译,并探讨艺术家如何在“临时共同体”的形成与艺术史叙事之间,处理由此产生的张力与交错。
12月6日,UCCA还将邀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常园青进行一次特邀导览“老去的共在”。活动将从衰老、照护与互依等角度切入,并以个体、群体与共同体三个层面回应展览内容,关注人们面对与适应衰老时的个人叙事,探讨代际协作带来的临时对话与共同实践,并将此延伸至社会场景中的实际行动,思考共老的未来如何在公共维度中构建。
展览文字
折页文章:在一起(或临时共同体)
田中功起
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探索“在一起”的问题,例如组织即兴的聚会,或者说,建立一些临时的共同体。与他人在一起,意味着暂时放下个人习惯,将自己投入到与他人或未知情境的协商过程中。共同在场——这个概念本身就充满了不可能性。大多数时候,我们要么彼此敌对,要么相互习以为常;要么分裂,要么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那么,是否可能在保持批判性距离的同时,仍然对他人保持开放?换言之,我们的潜力或许就存在于亲密友谊与对立敌意之间的某个区间。
最近,我受到“行星思维”的启发。我将其理解为一种打破习惯性思维边界的行动,让我们得以将目光投向整个星球(或“世界”)以及人类存在本身。在我的实践中,那些关于“共同在场”的情境,正是重新审视人类活动、反思人类关系的场域。我希望它能够打开一些机会,让人们说出不可言说之事,看到不可见之物,并承受我们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
关于影像的形式,我常这样想:一切动态影像都可以被视为人类活动的文献,从电影、YouTube 片段到手机视频等等。当人类不再存在时,未来的非人类(或外星的)考古学家或人类学家,或许会找到这些庞大动态影像资料中残留的部分,即便只是碎片。这些都将成为人类曾经存在的证据——我们曾经在场的痕迹。我也设想,我的作品最终或许也会成为这些遗存中的一部分。
带日期的笔记,或者类似日记 第 10 回
育儿与艺术实践── 2021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4 日
田中功起
女儿不知不觉已经一岁半了,正精神十足地到处走动。她把我和妻子都叫作“妈妈”(就在我校对这篇稿子时,突然开始叫“爸爸”了!);把手里的东西递给我们时会说“给银(给您)”;我们夸她“辛苦了”时,她还会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各种动作和词语总是不知从哪里忽然冒出来。我以为她是在托儿所里学到的,第二天早上送去的时候问保育员,却被告知没有教过这些。比如被叫到名字就举手的动作,也是没有人特意教,她就自己开始做了。
育儿虽然辛苦,但我从中感受到的乐趣也渐渐多了起来。和女儿一起翻看绘本很有趣。她总是拿过来好几本,这本读到一半就让我跳到另一本,而且我们从来不读到最后(因为已经读过无数次,早就知道结局了)。这种状态,就像在网上浏览文章。《好饿的毛毛虫》会突然出现在《睡美人》的荆棘丛中,大象巴巴在夜晚的森林里唱起关于月亮的童谣,《狗便便!》则和《气球猫》一起飞向天空。
还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编辑”故事。因为女儿坚持自己翻页,动作却不太熟练,所以常常一下子翻过好几页。于是,比如《桃太郎》的故事,会从“桃子顺流而来”直接跳到“桃太郎乘船前往鬼岛,从鬼怪手中夺回财宝归乡”的场景。但因为中间的语境被省略,读起来就像桃太郎和鬼怪的立场对调了。好像桃太郎不是退治鬼怪,而是带着一帮猛兽突然闯入原本安静的鬼岛生活,逼迫受伤的鬼怪们交出宝物。
“编辑”这样的行为,就是从眼前的材料里进行选择。挑拣、重新排列,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我一边帮女儿做着这些无意识的编辑,一边思考着育儿如何与艺术实践相连。
策展人的职能之一,正是从作品中进行选择、组合,并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今年,也就是 2021 年年初,我第一次以策展人身份在 e-flux 的线上平台进行策展 [ 田中功起,“Faraway, So Close”e-flux 影像项目,2021 年 4 月 19 日,https://www.e-flux.com/announcements/388880/faraway-so-close。另刊载于《ゲンロン α》(Genron Alpha)https://www.genron-alpha.com/article20210420_02/]。那是一个名叫“艺术家影像”的系列项目,邀请艺术家和影像创作者共同策划一个为期六周的项目,每周在线上播放一部影像作品。我选定的主题是我在这一系列连载中多次提到过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关系”。
伴随着过去这些年的特殊境况而出现的“新常态”等抽象词汇,使我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变得扁平;然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恰恰更应关注个体的具体生命。这就是我基本的策展思路。于是,我收集了与之契合的影像作品——有朋友的作品,有年轻一代的作品,也有历史性的影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让观众自己去发现其中的主题。影像主题包括二战时期日裔美国人被强制收容的历史(布鲁斯·米本和诺曼·米本,《Framed》,1989),在日韩国人领不到残障补助金的问题 (饭山由贵,《Old Long Stay》,2020),以及洛杉矶一家华裔美国人的丝绸店的店史(朱晓闻,《乡绸》,2015)等等。通过重新观看这些聚焦于具体生命的作品,我想我们也能有所裨益。
不过,选择并非策展人的专属。俄罗斯艺术评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在《多重作者》一文中写道,艺术家的工作已经从制作艺术品转变为选择它们。他追溯这种变化源于马塞尔·杜尚。杜尚被视为当代艺术的开创者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 1917年的《泉》。他将一个男用小便池横放,署名“R. Mutt 1917”,试图提交给他自己曾参与创立的纽约独立艺术家协会的首个展览。尽管这个展览没有评审委员会,但最终还是遭到拒绝。这一事件经过也成为了《泉》的传奇的一部分(而且原件已经遗失)。后来,杜尚把基于展示大批量生产物品的艺术作品称为“现成品”。根据格罗伊斯的说法,自杜尚以后,单纯的制作已不足以构成艺术家的行为。
“创造的行为已成为遴选的行为。换句话说,自杜尚以后,仅仅制造出某物已不足以使其制造者被视为艺术家。艺术家必须选择自己所制造之物,并宣告它是艺术作品。因而,自杜尚之后,艺术家亲手制作的物品与他人制作的物品,两者已经没有区别——两者都必须被‘选择’,才能被视作艺术作品。如今的‘作者’,就是做出选择并予以认定的人。杜尚之后,作者变成了策展人。艺术家首先是自己的策展人,因其选择了自己的作品。”[ 鲍里斯·格罗伊斯,《多重作者》,收录于《艺术的力量》,MIT Press,2008 年,第 93–94 页。]
是的,在当代艺术领域,艺术家就是策展人。即使没有像我在 e-flux 上那样策划有其他艺术家参与的展览,仅是“选择自己创作的作品并加以展示”这一行为就是策展。想象艺术家如何组织一次自己的个展就很清楚了:艺术家要考虑展示哪些作品、如何展示、为展览取标题、写展览陈述。这些是现在所有艺术家的一部分主要工作。
一开始,策展人是指主要隶属于美术馆、负责馆藏管理的人 [ “策展人”(curator)条目,泰特美术馆官网,参考链接:https://www.tate.org.uk/art/art-terms/c/curator]。这是其本职。而那种设定主题、选择作品并策划展览的“企划型策展人”,其实是比较近代才出现的。许多人可能听过瑞士策展人哈洛德·泽曼的名字。他在 1960 年代为进行装置艺术和行为表演实践的年轻艺术家组织过群展,主导过如“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1972)这样的大型国际展览,还曾为他的祖父策划了一场展览。正是泽曼将“制造展览”从单纯的博览会式陈列,转变为一种表达方式。这种体现策展人思想的展览形式,可以说是泽曼开创的。以这一转变的巨大意义来说,泽曼甚至可以被称为艺术家。事实上,在他于 2005 年去世后,已有多部关于他的专著出版,他的策展实践至今仍影响深远。像我这样把展览制作视为自己艺术实践一部分的艺术家,可以说也是在他影响之下行动。
泽曼带来的转变始于 60 年代。因此,与其像格罗伊斯所写的那样,解读为“杜尚让艺术家变成了策展人”,不如理解为:艺术家率先将“选择”的行为带入艺术实践,而策展人的工作重心随后从馆藏管理转向了展览制作(对作品的“选择”)。这里有趣的一点是, e-flux 的项目其实并没有使用“curation”(策展)这个词,而是用了“convened by”,也就是“由……召集”。
并非是选择,而是集合。
我也希望把自己在 e-flux 所做的事理解为“召集”而不是“选择”。或许你还记得,在这个连载中我曾写到,“选择”的对立面是“关怀”。让我们再次参照人类学家安玛丽·摩尔的《关怀的逻辑》(Routledge 出版社 , 2008)。她在书中将“选择的逻辑”与“关怀的逻辑”进行对比。如果说选择基于自主的个体,关怀则基于相互依存的集体。前者可以说是“强主体”,后者是“弱主体”。请试着想象一位不拥有强烈个性、依赖型的“弱”艺术家,与一位拥有鲜明个性、独立型的“强”艺术家相对比,会是什么样子。
自己进行创作的艺术家,拥有独立而强大的个性,会在作品上留下署名,推广自己的名字。而像杜尚这样进行“选择”的艺术家,也有强烈的判断标准,他们会在自己策划的展览上署名,并推广自己的名字。比如泽曼,他的名字往往比参展艺术家更在历史上留名,这正是因其策展的个性。可是我想探索的,既不是“创作者”,也不是“选择者”,而是一个也许可以称之为“依赖者”的、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立足的艺术家。他们会寻求合作者、顾问、专家的帮助。我想我自己也是如此。最终,创作会以集体合作的形式完成。
但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家群体”。请你想想,大多数艺术家群体其实是强烈个性的聚合体,他们的团体名称会像艺术家署名一样传播,还会以团体名义举办个展。即使是群体,本质上与个体艺术家并无不同。
另一方面,依赖型艺术家总是独自一人。作为弱主体,必须不断寻求他人的帮助。集体性只是结果,是不得不产生的。因为一个人什么也做不到。我试图要将这样的状态视作积极的。
集体并非选择取舍的结果,也可能只是偶然被集合。有时,集体并非出于主动选择,而是源于被动地接受。然而,被动并不一定是坏事。它意味着接受自身能动性的限度,并对现实形成一种清醒的自觉。
育儿生活,就像被卷入强烈的激流中,在还来不及思考的情况下不断地挣扎,每天只是在努力不让自己被吞没。你根本没有余裕去选择“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因为孩子会飞快地成长到下一个阶段,总是有新的情况需要应对。完全没有时间经过思考和认同再做出选择,只能不断地被动接受。但正如我开头所说,共同经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实在是非常美妙的事。
这种认知也深刻影响了我的创作。当我的生活以育儿为中心,意味着创作风格和方法也必须随之调整。能工作的时间变得非常有限。一位有育儿经验的朋友曾建议我:在育儿的空隙里,哪怕累了或者没心情,也要赶紧工作,因为不知道下一次 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如果想着“以后再做”,往往就会遇到孩子突然生病需要去医院,或者夜里要忙着哄哭闹的孩子,“以后”常常不会来。如果不见缝插针地工作,可能就没办法工作了。
面对时间的匮乏,我首先必须接受的是作品“质量”的下降。不能无休止地耗时在视频剪辑上,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内完成即可。就算“质量”比以前有所下降,也无可奈何。
读者们看到这里会不会感到失望?
但是,放弃以前精益求精的执念,不再一直拖延到“有了灵感”再工作,而把孩子的健康放在首位——这是理所当然的。比如说,如果为了剪辑视频而把带孩子去医院放在次要位置,这是不可接受的吧?那么,原本拼命维持的“质量”究竟是什么?也许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我所执着的“质量”,到底是什么?花更多时间和精力,也并不一定能维持“质量”。相反,应当这样理解:有一种新的“质量”,只能通过现在的育儿生活获得。
前些天我策划了一个关于歧视这一主题的虚构电台节目,邀请了我的老朋友、社会学者韩东贤(Han Tonghyun)先生,为东京造形大学的学生讲授关于歧视的基础知识(种族主义、微歧视、“仇恨言论对策法”等)。歧视基本上是社会结构的产物。这个社会(日本)本就是为了多数人而设计的,因此必然会排挤少数群体。韩先生举了“楼梯”的例子。我们习以为常地使用楼梯,觉得上二楼需要楼梯,因此建筑中就会设置楼梯。这说明建筑是根据健全人的身体设计的。另一方面, 电梯则是为轮椅使用者等设置的。如果以所有人都使用轮椅为前提来设计社会,不管几层的建筑都理应安装电梯。因此,应该把“为轮椅使用者设置电梯”,看作与“为健全人设置楼梯”相同的逻辑。也就是说,要把社会从多数人的最优,转变为少数人的最优。
我之前提到过自己的经历:推婴儿车时,我总是关心车站的电梯在哪里。但是,电梯往往在站台的尽头。这让我开始注意到,不仅是推婴儿车不便,轮椅使用者也同样不便……这也和我以前提到过的安玛丽·摩尔的“病患主义”有关。不应以健康的身体为前提来设计社会,而应该以病弱的身体为前提。“病患主义”主张,不是让病弱者去适应健康者,而是以患者的身体为基础来建立社会基础设施。患病本就辛苦,若道路、电梯经过设计能稍稍减轻这种辛苦,谁会不同意呢?我自己在做脑外科手术之后,连走路都很艰难,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电梯、自动扶梯。人群带来的视觉刺激也很难忍受,于是我一边规划安静的路线一边移动。我真心希望社会能以这种身体为前提来运作。
我们要以什么为前提?要优先什么群体?考虑这些,就能让社会发生巨大变化。
当一种疾病从流行病发展为大规模疫情,最终转化为地方性疾病,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它不是季节性的流感,而是全年持续,应对起来确实艰难。口罩可能要成为日常道具。
再回到我自身的艺术实践。我的创作以什么为前提?我的生活是以孩子为前提的,创作也是如此。正如我之前所写,每天能工作的时间有限,再也不能说走就走地参加国际驻留。必须要接受这些“做不到”的限制,事实上我已经这样做了。比如举办对谈或会议,我就必须安排在孩子在托儿所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当然,这对观众来说不容易。但换一个时区,对海外某些地区可能就正好合适。再加上疫情让远程会议成为常态,也算方便。或者,孩子睡着后的晚上 9 点、10 点之后也可以。比如前几天,伦敦(下午)的基金会策划了一场对谈,把在纽约(早晨)的策展人和在京都(晚上)的我进行连线通话。通过这样的时间调配,工作还是能进行的。
创作时间虽然减少了,但正是从这种现实的经验出发,才可能发现此前未曾注意的事物。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孕育新的创作方式、作品想法,以及另一种不同的“质量”。
在一次会议中,我说过:我对“关怀”理论感兴趣,是因为育儿生活太辛苦,某种意义上我也试图在理论中寻求庇护。于是有参会者建议:如果要策划一个关于关怀的活动,那还需要一个没有在关怀理论中寻求庇护的主办人。大概他把我的“理论庇护”理解为:我在逃避甚至不想承担实际的育儿责任,而只思考理论。但大多数“关怀理论”本就源自现实问题。而我的女儿就在我眼前走来走去,育儿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字面意义上,我根本无法“逃避”。我想说的其实是,在理论与混乱的生活之间往返。但或许,他人未必可以理解。
某种不同于以往的“质量”,或许会在有限的时间里,在那短暂的专注中产生。为了增强这种力量,需要理论、需要创意、需要巧思。写下这些日记般的文字,对我来说正是一个整理思考的场域。写作、创作、选择、依赖。在这重构的日常中, 我用身体经验、用新的思考与技术,依然能开拓新的视角,依然能有所作为。我希望,我的艺术实践可以与刚刚开始学步的女儿一起,由此开始新篇章。
之后会怎么样呢?
嗯,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吧。
本文原载:田中功起,《带日期的笔记,或者类似日记 第 10 回:育儿与艺术实践——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4 日》,《ゲンロン β68》(Genron Beta 第 68 期),Genron 株式会社,2021 年
主题文字
1. 延展的临时性
临时性是田中功起创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构成了此次展览的关键线索。展陈设计上不加粉饰的板墙、外露的支架、随意张贴的海报和自由摆放的椅子——像是构成某种暂时的聚集,让人联想起灾后临时建筑、应急避难所,或是因为无法外出而衍生的居家露营。这些场景指向生活中不期而至的危机事件及随之自发形成的临时互助共同体。经历过例如“3·11”日本大地震等公共危机后,田中愈发关注这一议题,并开始将组织实验性的临时集体作为创作主题。最具代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他分别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人聚在一起,将习惯上被认为只能由个人完成的行为——弹琴、制陶、写诗等,转化成多人同时完成的尝试,以此探索过程中的协作张力与创造潜能。田中将创作的过程留给参与者,自己不去干预而只是促成并记录这些临时的集体性时刻。
他的近作则转向无明确任务与叙事的工作坊。例如在《抓人游戏》(2024)中,参与者不断进行带有肢体接触意味的游戏,同时朗读自己在流行病期间的经历。此次展出的由UCCA参与委任的最新作品《十年》(2025)则将一群2015年曾参与他作品的高中生再次聚集在一起,彼此分享他们过去十年间的变化与感悟。艺术家希望通过这种松散的、游击式的临时集体,打破既有群体的僵化与停滞,促使个体在开放对话中协商与探索,以形成应对变动世界的动态法则。
2. 编辑作为方法
田中功起在作品中将“编辑”视为一种具有作者性的创作方式。对他而言,编辑不仅是创作手段,更是一种开放的姿态。通过编辑,艺术家、材料与观众可以共享作者身份。同时,它也提醒我们:历史本身始终处于可被阐释与理解的可能之中。
开始作为艺术家投身创作之前,田中曾担任艺术杂志的编辑。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对意义生产的认知:意义不仅源自对新内容的创造,也来自对既有素材的重新编排。他的影像与写作并不依循线性叙事的结构,而是经过重组、叠加与并置完成,凸显了编辑作为意义生产者的角色。
田中的创作理念呼应了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将文本比作“碎片织物”的观点。艺术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唯一的意义源头,而是将创作权重新分配给构成其作品的参与者、情境与日常行为。于是,编辑和剪辑不止作为技术步骤,也被用于揭示意义是如何在“碎片”之间、在人与人之间生成。
这一逻辑也延伸到了展览现场。面对田中的作品时,观众们同样成为编辑者:留意细节的差异,串联各个作品的碎片,用分散的元素构建自己的解读。由此,展览从一段既定的故事转变为一个开放可能性的场域——在这个空间,意义通过选择、关注与排列组合的行为被协作性地创造。
3. 演绎真实
纪录片通常被认为呈现的是拍摄对象“自然”的日常行为。然而,正如迈克尔·雷诺夫与斯特拉·布鲁齐等理论家所指出的:无论是由于拍摄者的操控,抑或拍摄对象的自我意识,摄像机总会使其试图记录的现实变得更为复杂。田中功起通过他的影像实践,清晰揭示了这种不稳定的再现机制:参与者在影片中朗读自己事先写下的台词,有时直接在镜头前手持剧本。通过坦诚地展现剧本编写与表演的过程,艺术家呈现出一种另类的真实性——它并非源于自发的即兴发挥,而来自于展示自我是如何被构建与表现的。此外,他还经常邀请参与者互相拍摄,从而打破“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二元关系。在《迁徙与毁灭》(2024)这样的项目中,这种流动的角色生态使纪录片不再是透明的记录,而是一个表演、交换与权力都可以进行协商的场域。
田中近期的作品《表演即分享自我》(2025)标志着他创作方法的一个转折。早期项目直接调用参与者的亲身经历,而本次他首次邀请了职业演员出演,台词来自田中对东京大丸有地区(中心商务区)上班族的访谈。个人经验经由演员的身体与声音被重新表述。由此,田中强调纪录片的拍摄对象并非意义的唯一源头——它只是持续的中介化过程的一环,经过编剧、剪辑与表演呈现。主体性在过程中不断被重构。在这个意义上,田中不仅动摇了纪录片真实性的幻象,更挑战了个人叙事与作者身份的边界。他的作品提醒我们:编辑从来不是中立的操作,而是一种具有生成性的行为——意义、身份与历史在其中被不断重塑。
4. 日常作为锚点
田中功起在他的创作中持续探索日常行为的可能性,并将此作为抵抗日益占据我们生活的抽象化概念的锚点。这样的关注回应了他所处的一代人在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面对长期衰退的社会现实时的处境。他们不再关注宏大叙事,转而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琐事并从中寻找革新的可能。此次展出了多件呼应田中功起这一思路的早期作品,例如《一切一切》(2006),他以不断重复的动作测试、探索日常物品,例如衣架、杯子、床垫的物理特性,由此产生的记录行为或荒谬或单调,抑或在某个时刻引发顿悟。
2009年移居洛杉矶之后,田中开始专注于探索日常的人际交往行为,他通过创造一些不同寻常的集体合作情境,记录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无意识呈现的行为,以此来探讨在微观社会和临时社群中所产生的群体动力。而他近期作品虽然多以大型的社会事件或全球性的动荡现象作为讨论的起点,但是依旧从最为具体的人和事物入手,体察个体在其中所经历的困境和感悟。他还常常以日记或随笔的形式来记录日常经验,并将其视作创作的一部分。例如因女儿的诞生而让他开始关注育儿的话题,并将其与自己的艺术实践相关联。由此写作的文字以及他平时用手机拍摄的育儿片段,也在展览空间中以展览作品与展陈设计的方式呈现。
5. 关怀与照护
无论是近年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还是个人的育儿日常,都让田中功起意识到关怀与照护——这个在历史上被视为女性化、进而被忽视的视角——是如此的重要。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经历照护者和被照护者两种身份的流动,非依赖的状态反而是人生旅程中的例外。这也成为他近期创作的核心议题。在《省思笔记(重组)》(2021)中,田中功起以日记般的旁白与日常影像,坦诚分享过去几年的防疫政策,让他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关怀与接触的意义。另一部作品《迁徙与毁灭》(2024)则将这个议题扩大到对于全球性动荡不安的社会处境的探讨。散落在展场中的照片和文字,记录了他对于自身育儿实践的分享,从不同的维度体现了田中功起不断在作品中探讨一种基于相互依赖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对生命境况的体察。同时,他将这样的思考与实践,拓展到劳动分工、歧视与偏见、生态与社会危机等议题。通过对于照护理论的关注,直面彼此的脆弱与当下的不安定状态,并期许一种变革性的人际关系与关怀的政治。